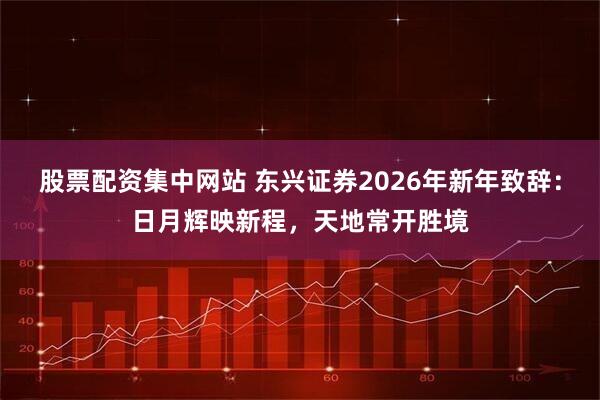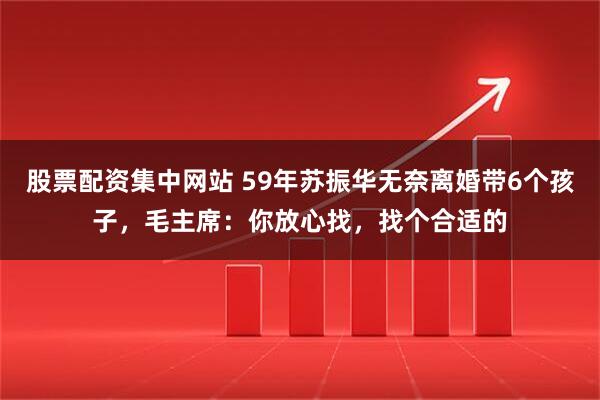
“1959年初春的夜里股票配资集中网站,北京还是透着寒意。”秘书张诚推门进来低声提醒,“苏政委,您该休息了。”屋里烟雾缭绕,苏振华靠在椅背上,把处理到一半的离婚报告压在膝盖上,眉头紧锁,没有抬头。那一年,他四十七岁,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却要在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面对另一场不会流血的战斗——守护六个孩子的完整与妻子孟玮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

追溯到二十年代,平江山沟里出身的苏振华似乎从来不缺艰难:幼时几乎饿死,少年给地主做长工,十九岁携带母亲的嘱咐仓促成婚,又转身投入红军。那一纸婚书是母亲争来的安全符,他本人却只和余姣凤相伴了一个夜晚。此后的漫长路途,上井冈、闯赣南、跨草地,一次次死里逃生,再想起故乡时,消息却是妻子已因饥饿与折磨倒在1935年的冬天。说不出沉痛还是麻木,苏振华只是把写给家乡的信塞进衣袋,继续行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抗大迎来一批批年轻人。教员讲军事理论,山沟里的粗汉子却第一次想起“爱情”两个字。孟玮就是那时走进他视线的:眼神清澈,字写得端正,枪也打得准。两人搭班突击整理教案,夜里借着油灯抄写教材——有意思的是,谁也没主动开口表白,罗瑞卿一句“都不是孩子了,干脆结婚”,倒像一声令下。战火下的婚礼从来简陋,但延安窑洞里一碗臊子面、几句祝福就足够隆重。
三年游击、三年解放战争,夫妻俩几乎寸步不离。枪林弹雨中接连有了六个孩子:老大出生在太行山,老二在平原的地窖里呱呱坠地,老三老四赶上辽沈,老五老六已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礼炮。孟玮擅长打绑腿,也能缝补军装,却没时间照料自己的情绪。国旗升起后,外表坚强的她终于松弛下来,却在1954年苏振华调往海军后,悄悄陷入深渊。
海军机关事务繁杂,苏振华一年有一半时间漂在各舰队检查。孩子们住进北京海军大院,可孟玮开始怀疑走廊里有人跟踪,时常半夜惊醒。最初大家以为是劳累后的小毛病,谁料谵妄越发频繁。一次她神情恍惚地说:“那位同志总在窗外盯着我,我不走,他就不走。”苏振华一遍遍解释“窗外没人”,孟玮却焦躁到摔杯子。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药物只能暂时安抚,她却执意搬出家门,甚至提出离婚。
苏振华先后找过罗瑞卿、萧劲光商量:“是不是把她接到上海疗养?”组织很快批示同意,可疗养院的幽静又让孟玮愈发自闭。孩子们一次次去看母亲,她却连名字都叫错。儿子老大回来说:“爸,妈说她要去找那个人。”那一刻,苏振华沉默良久,只问了一句:“她笑了吗?”得到否定回答,他把探视的日期又推迟一周,生怕刺激加重。
1958年底,孟玮写来一封字迹凌乱的信,反复强调“给我自由”。心理医生建议:若病人坚拒配合治疗,可暂时顺其意,减少对抗。于是才有了那张离婚报告。苏振华仍在犹豫,文件一次次退回补充材料,直到1959年3月,他看到孟玮在病房用指甲在墙上刻“走”字,终于签了名。
手续办妥后不久,他受邀去中南海汇报海军训练。毛泽东听完公事,突然问:“听说你带六个孩子?”苏振华点头。主席放下茶杯,语气轻却带着关怀:“放心找,找个合适的,人要活得开阔。”一句话并非劝再娶,更像准许他继续肩负生活的重量。会后,周围人劝他抓紧物色对象,他却先写信给孩子们:“娘永远是你们娘,她病了,我们要照顾她。”
接下来几年里,生活在两条平行线延伸。孩子们轮班把补品和药费送到疗养院,苏振华照例在油灯下批文件。面对海军现代化的巨大缺口,他既要学苏联教材,也要抓国产舰艇试航。没人看到的是,他常把工资条摊开,扣除家用、母亲赡养费,再分出一半寄往上海;剩下的钞票塞进旧皮夹,转天照样出海。
1963年,经同事介绍,二十四岁的陆迪伦出现在海军招待所的客厅。这个浙江姑娘大学毕业,谈吐得体,见面第一句竟问:“听说首长会做平江腊肉?”一句俏皮话让年近五旬的苏振华笑出了声。随后几个月,相处平静无波,陆迪伦对六个孩子颇有耐心,也不回避那段难言的往事。组织审查无异议,两人便登记成婚。婚礼仍旧简单——一盘腊肉,一壶老酒,几位老战友在旁边鼓掌。
陆迪伦接手家庭后,孟玮依旧被妥善安置,探视频率从未降低。遗憾的是,孟玮的病情已难逆转,意识清醒时极少。后来海军司令部一位医务处干部回忆:“苏老总每次托人捎东西,都强调‘别提他名字’。”有人不解,他苦笑:“她要是半梦半醒听见我的名字,更难过。”
时间推到七十年代,苏振华升任要职,从未在公共场合提及家事。走访基层舰艇时,有青年军官问:“首长,打仗苦还是带孩子苦?”他停顿片刻,只回答一句:“各有千斤,别怕,扛就是了。”旁人只当幽默,却不知那是他数十年生活的提炼。
1985年,苏振华病逝。遗嘱里除了要求葬回平江,最醒目的一句是:“六个孩子继续照顾你们的母亲。”那年孟玮已沉睡在疗养院的花园深处,时而抬头看天,时而低头发呆。谁也无法确认她是否知道那位曾经并肩走过烽火岁月的丈夫已先一步离去,只能肯定——在她昏暗的记忆里,或许仍有北方窑洞里那碗热乎的臊子面,和夜里淡淡的油灯光。
2
我要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